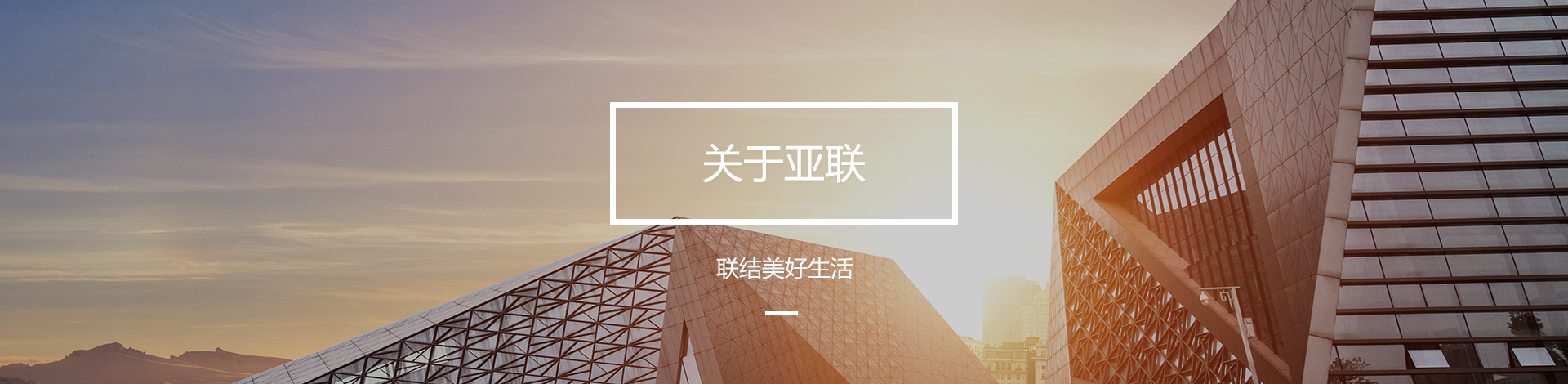


2018-10-29

2287
最近以北京为首的国内大城市房租飙涨引发热议,原我爱我家副总裁胡景晖指责自如、蛋壳等长租公寓运营商为了扩大规模,以高于市场正常价格的20%-40%的价格哄抬租金抢房源,导致租金暴涨;紧接着,蛋壳公寓执行董事长董博阳和自如CEO熊林坚决否认哄抬房租,认为中国一线城市的租住供需已经完全市场化,长租公寓公司市占率不大,无法垄断供应,决定价格。
这几天,大量文章和评论铺天盖地充斥媒体和网络,围绕房租暴涨原因和后果唇枪舌战,争论不休,似乎都没说到点子上。其实根本用不着争,数据说话。北京上海常住人口近两年不但没有增长,由于政府有意控制反而略有减少,正常情况下每年都有新房销售,总房屋供应量是增加的,按理说供求关系应该趋于缓和,不应该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需求结构上因为人均收入的增长低于GDP增速,不到7%,也不可能引发房租高达30%的暴涨,以上数据只能意味着供给总量和结构在短期产生了剧烈的边际变化。
谁推高了房租?
总量方面,与自如同属链家旗下的贝壳研究院将原因归于拆违行动导致房源供应紧张,“近来北京市集中清理与拆除违规公寓、群租房以及隔断房等不符合消防安全的租赁住房,导致市场上低端租赁房源减少,同时对黑中介、二房东的打击导致部分不合规房源下降,挂牌房源总数下滑;此前低端房源的租客不得不转向收费更高的其他产品类型,需求端的增长推动了这部分产品租金上涨。”据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至17年,北京市拆违面积分别是1818万平方米、3000万平方米、5985万平方米,今年前4个月已达1641万平方米,拆除量是去年同期的3.8倍,北京统计年鉴显示,住宅存量面积也只有5亿平米(该数据存疑,不过即使10亿平米也不影响结论),这样运动式的拆违带来供给的急剧减少,后果可想而知。而同时,2018年上半年,北京商品住房累计成交157万平米,较去年同期下降35%,较去年下半年下降21%,跟拆掉的面积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结构方面,长租公寓的介入在原本相对扁平和分散的租赁市场中间增加了一个环节,不仅提高了中间费用,而且造成了诸多衍生问题。资本推动长租公寓超常规发展,仅蛋壳公寓在今年内就拿到了1亿美元的A轮和数亿元人民币的A+轮融资,规模是这类互联网模式企业发展初期的核心诉求,赢家通吃是基本玩法,业内计算20万间是生死线,所以千余家长租运营企业必然拼命跑马圈地,舍命狂奔,抬高市场价格抢房源既合乎逻辑,也有大量证据。长租公寓运营商们的入市和白热化竞争迅速生成了一个原来没有的中间需求市场,抬高了租金水平,然后又令原本极度分散的供给市场集中度突然大幅提高,作为最终需求方的租客的议价能力被大大削弱。
事实非常清楚,无论是希望减少低端房源以控制城市人口还是无意为之,城市管理者超常规拆违客观上制造了供给紧张,给运营商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而长租公寓运营商们的自辩清白在无数高价收房的证据面前也显得苍白无力,北京市政府约谈几家企业当场就答应释放10万套存量房,说明它们不仅为扩张规模而抢房,房价上涨于它们也有利可图。跟操纵股价一个套路,不需要把所有流通股都买下来,拉升前低吸到足够多的筹码,用各种手段做市就可以四两拨千斤撬动整个市场获得暴利,有的是人跟风。在一个供求紧平衡的市场中,上涨预期很容易形成,(反之亦然),只要需求(或供给)有足够的刚性,人为囤货制造一点短缺和恐慌,价格很容易持续飙升,这在无数行业里都有过典型案例,大宗商品、海运价格动不动就是数倍甚至十几倍的涨跌,其实这后面的每年供求波动仅仅百分之几而已,红木、艺术品、普洱茶、蒜泥狠姜你军等等都是如此,有的是由于市场比较狭窄,容易被垄断定价,有的是因为流动性不充分,定价模式是参与交易的部分边际定价而巨大的存量不参与定价,比如租房合同一般一年甚至数年一签,平均到每个交易日的成交量占比不高,但正是这不大的成交量决定了市场价格,而操纵者仅需在这不大的成交量中占不大的份额并对其他交易施加影响,比如释放强烈的看涨信号,就可以起到影响市场的作用了,股市楼市都因此而较易被阶段性操纵,这类牵涉到国计民生的市场也就特别需要政府监管,以维护市场的稳定。
数据背后的真相
然而事情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数据背后还有真相。就像房价上涨不仅是“无良奸商”和“土地财政”合谋的结果,租金的上涨也不仅是市场和政府共同导演的好戏,房价和房租无休止上涨难以遏制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资源配置机制,简言之,是北京之所以被称作“帝都”,上海之所以被称作“魔都”的根本所在。那么多人抱怨不迭咬牙切齿,仍然挤在几平米的蜗居里继续北漂沪漂,是因为对这些人而言,只有北京上海才有希望,家已经回不去了,“回去了如果当不上公务员就很难有像样的工作,还不如留在北京”(精辟的网友留言)。政府配置各种资源的支配力越强,马太效应就越明显,政治中心北京的地位就越无法撼动,钦定的金融中心上海深圳和各省的行政中心的虹吸效应就越显著,教育、医疗以及几乎一切必不可少的资源就不得不围绕这些中心进行配置,从而形成更强大的竞争优势,其他城市完全没有与之抗衡的基础,低线城市和农村的凋敝就成为必然。有券商就高铁沿线低线城市开通高铁前后经济相对实力的实证研究清楚地揭示了这个规律,高铁对他们并非福音,反而为这些地区的人们提供了去大城市生活、消费和工作的便利。如果不继续简政放权深化改革,华盛顿、渥太华、堪培拉、比勒陀利亚这种大国家小首都的情况和地区之间、各地区内部发展相对均衡的理想局面是很难在中国出现的。
房租将接力房价成神话?
房租暴涨的后续和影响如何?很多人得出如下结论,最终,不合理的低租售比以租金报复性上涨的方式托住了房价,且为房价的继续上涨奠定了基础,高房价风险解除。对此我不敢苟同,窃以为,租金的暴涨不可持续,如果处理不当,反而可能为房价泡沫的破灭指明了路径,敲响了丧钟。
从微观层面理解供求很难看懂周期变化,看不出房价有下跌的理由,然而宏观的高杠杆和结构上金融地产对实体经济的挤压导致头重脚轻不可持续,金融周期逼近顶部,租金上涨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地产对实体的盘剥,成为促成拐点到来的最后一根稻草。
即使不考虑经济波动,租房人的数量减少,留下来的人又持续被房租上涨剥夺了房子的购买能力,购房的潜在需求当然会大打折扣!有人说貌似房东获得了更多收入,会有更多消费,要知道,把城市当做一个整体,在出租率不变的前提下房租涨跌不影响整体收入,是个零和游戏,城市的经济不会因涨租金受益,反而会因上述原因而多方面严重受损。因此,不那么糟而且大概率会发生的情况是低收入者被赶出大城市,需求减少,跟股市过山车一样房租快速回落,实体经济虽有波动但总体可控。
万一房租高烧不退,病情就恶化了。房价高企影响实体经济的投资和消费,但该影响还相对间接,房价的上涨只要不传导到房租,就尚未构成对生活成本和经营成本的直接压力,个人和企业可以不买房,但是都必须租房,租房才是真正的刚需,是CPI的重要组成部分(奇怪的是官方统计的CPI中居住费用指数始终平稳,跟房租的上涨似乎毫无关系),所有市场参与者的成本都必然跟着房租水涨船高,无一能够幸免。单拿薪酬举例,员工刚性生活成本上升,不给员工涨工资留不住人也招不来人,涨工资就要亏损,横竖是个死,这样的环境实体经济本来就利薄如纸,如风中之烛,哪里扛得住一下子30%成本上涨的冲击!我们所谓大国经济的韧性届时将荡然无存,人力成本和房租成本的快速上升会极大削弱中国制造的优势,连华为都分几批从深圳搬到东莞降成本保优势,其他企业可想而知。最糟糕的可能性(虽然概率不大)是房租持续大涨反过来强化房价上涨预期,进一步提升投资性购房需求,这种死灰复燃虽然很短暂,但也很致命。企业必须转嫁成本才能生存,通胀在所难免,而且很难通过货币手段来控制,成本全面上升引发的通胀最后将演变为滞涨,经济下行、实业和通胀高企,其时无论是房价还是房租都将因其给实体经济施加的压力而遭受反向冲击,无论金融地产还是实体经济,势必元气大伤。
纯理论探讨,简单延展一下结论,大城市的房价和房租都会远高于低线城市,但任何城市的房租涨速均难以长期超越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在租售比的分子分母之间,拉长看,房价对房租的向上拉升力远不如房租对房价的向下吸引,因为租才是基础,人均收入和实体经济才是本质。房地产市场无比复杂,需要讨论的点和值得观察的角度非常丰富,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房价大跌是中国经济最不能承受的风险,因此包括众多专家学者在内的人都认为这不可能发生,政府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房价,哪怕冻结楼市,不让交易。然而价值回归是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你想出任何办法都不可能改变。租售比类似于股票的市盈率,一线城市1.5%的租售比相当于65倍市盈率,代表房价预期稳定前提下买房的收益率,是衡量房价合理与否和楼市投机程度的标志,长期一定会与市场利率相匹配,因为市场参与者会比较各种投资品种的收益,理性选择。当前低租售比的形成来源于房价上涨预期,无论政府严控房价上涨能不能改变这个预期,租售比都必将回归合理。且由于未来的购房刚需都来自于当下的租房者,按照现在限购城市的规定,没缴满几年社保是不具备买房资格的,租售比又体现了供给和潜在需求的关系,低租售比也反映了潜在需求群体的承受能力与房价脱节,高房价未来缺乏刚需承接。
租售比的回归方式
难以长期持续的低租售比有三种回归方式,一是大放水,让市场利率水平大幅下跌,租售比就显得合理了,(前提是不能开征房产税,因为那会令购房的收益率为负;而且放水也可能让房价的涨幅大于房租,所以说也未必能降低租售比),这在去杠杆的环境下无异于痴人说梦;第二种是房价大跌,第三种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租金大幅上涨。上文已经分析过,租金大幅上涨得以持续不仅需要承租人的收入水平能够快速提升,而且还需要实体经济能承受成本的快速上升,否则将成为一场灾难。就像地震由震中向周边扩散,强度快速衰减,被波及的地区虽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然而受灾的严重程度完全无法跟震中相提并论,何况最后如果被迫让实体经济成为震中,地震的强度将远超单纯的以金融地产为震中的危机。后一种情况好比2008年的汶川8级地震,的确惨烈,但因人烟稠密经济发达的城市不在震中,恢复重建都相对容易得多,前一种情况则堪比在大都市的市区发生一场十级地震,它可能引发长期的衰退,经济的核心和整个生态都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想恢复都难。
所谓单纯的金融地产危机是指房价和负债率过高了以后顺应市场规律自然回归,冲击有限;实体经济危机则是因不愿承受这种冲击而刻意维持甚至进一步推升高房价和高杠杆,对实体经济造成长期和实质性的损害,并最终导致全面崩溃。杠杆高的危害不需要用高深理论解释,炒期货比较容易爆仓就因为期货杠杆高,控制不好仓位则完全经不起微小的风吹草动。人民大学研究显示居民部门的负债率已高达110%,超过美国108%的水平,大部分负债都是房贷,而且很大比例是近三年增加的,现在经济减速人口老龄化,正如年轻人借多点债还可能还得起,你都退休了拿什么还?降杠杆刻不容缓。高杠杆和高房价是一体的,互为表里,去杠杆的同时也必须降房价,否则不解决本质问题,就像减肥,好不容易饿得满眼金星掉了几斤肉,一不注意体重反弹创新高。最理想的状况是政府有能力逐步扭转市场预期,引导房价平稳回调,尽管难度极大,只要足够重视,希望还是有的。可如果房租高居不下,主动降房价就变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上一篇:没有了 下一篇:没有了
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分享到其他
0755-26520661


